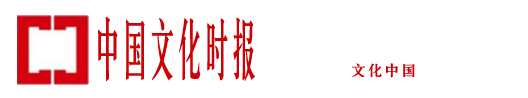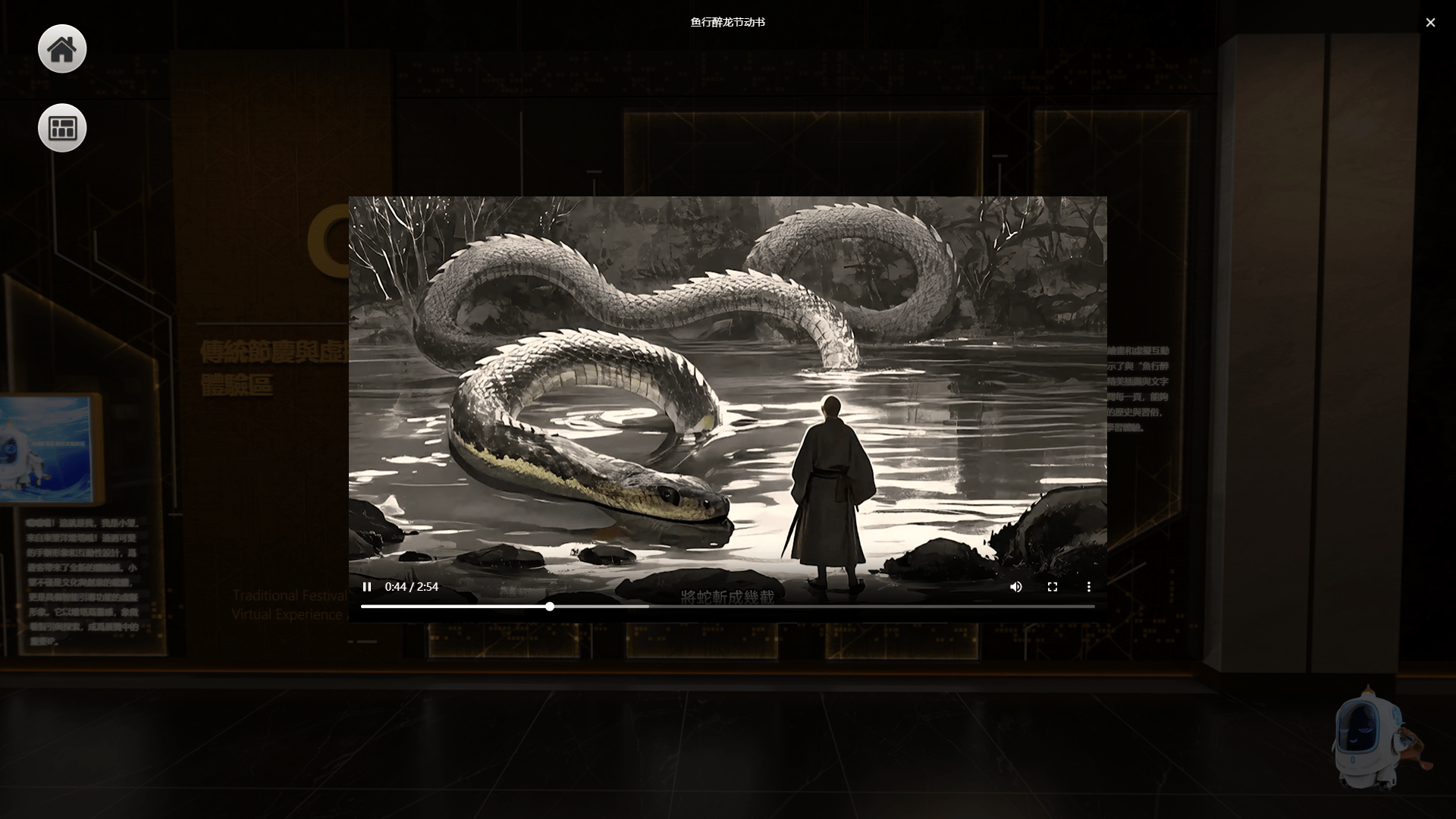内容简介
本书是艺术家王钧先生的个人自传,讲述了一个黄土高原农家子弟如何遵循内心召唤,通过书画艺术实现自我价值,最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的非凡历程。从十二岁的神秘体验到为国士创作传承之画,从浙江的艺术市场探索到北京国庆观礼台的荣光,作者用真挚的笔触展现了"奉天承运"的深刻内涵——个人天赋与时代使命的完美结合。
序言:天命之叩问
万般皆是命,半点不由人?我命由我不由天?
“天命”二字,自古便是最宏大又最私密、最必然又最飘渺的命题。
它究竟是高悬于上的注定,还是深埋于心的召唤?是外部命运的强力安排,还是内在灵魂的主动选择?
我的人生,似乎从一开始,就为这场永恒的辩论提供了一场微妙的见证。
我的根,深植于陕西韩城那片被岁月浸透的黄土塬上。父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,他们用最质朴的劳作教会我何谓"脚踏实地"——这是土地赋予我的第一重底色,沉静而坚韧。倘若命运仅止于此,我的人生轨迹或许将如祖辈般,沿着田垄的走向,清晰而平稳。
然而,天命从不甘于单一的回答。
于是,它为我安排了另一位"代言人"——我的爷爷。一位从市里毅然返乡,在村支书任上一干就是二十年的知识分子。从他的书房里,我触摸到的是一种"胸怀天下"的责任与格局。这还不够,天命又慈祥地为我添上另一笔浓墨重彩——我的外公,一位奔走乡里、妙手回春的兽医站长。从他身上,我学到的是"一技之长"的尊严和"悬壶济世"的仁心。
于是,在我的童年里,土地的厚重、书页的墨香、药箱的温度,奇妙地交融在一起。我既是田埂上奔跑的野孩子,也是书房里安静的聆听者,还是出诊路上小小的跟随者。
作为家族的长孙,我集双份的宠爱与期许于一身。这份独特的身份,早早地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:我的人生,似乎不应仅仅是为了自己。它理应承载更多,回应更多。
我常常自问:我究竟是谁?是农民的儿子,恪守本分?是知识分子的后代,求索真理?还是医者的传人,疗愈伤痛?这些看似迥异的角色,在我体内碰撞、融合,最终汇聚成一个持续终生的叩问:
我的"天命",究竟何在?
它并非一个等待被揭示的既定答案,而是一场需要我用一生去践行、去验证的探索。这本书,便是我交出的答卷。
这不是一个成功学的范本,只是一个真诚的生命记录。其中有意气风发的顺境,更有迷茫挣扎的低谷;有看似命运眷顾的机缘,也有非如此不可的倔强选择。
因为天命,从来不是宿命的判决,而是命运的邀请。
它始于根脉,显于抉择,最终成于每一个"我"毅然踏出的那一步。
——根脉篇——
第一章:根脉与萌芽
第一节 黄土塬上的家
我的生命起点,位于陕西省韩城市西庄镇杨村。这是一片被厚重历史与黄土文化深深浸润的土地。对于外面的世界而言,它或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地名;但于我而言,它是我认知这个世界的原点,是我"天命"航程的起锚之地。
我的家庭,一如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家庭,平凡而质朴。父母是地道的农民,他们的命运与土地紧密相连。日升而作,日落而息,他们的双手因常年劳作而粗糙,却无比温暖有力。从他们身上,我最早学到了"勤劳"与"坚韧"的含义——那是黄土赋予子孙最基础的底色,是沉默的、无需言传的身教。
第二节 门风两脉:耕读与济世
我很幸运,在童年时期便接受了两种不同维度的滋养。
一脉来自我的爷爷。他是我童年世界里一位"大人物"。与父亲纯粹的农人形象不同,爷爷是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。他曾在市组织部、税务局担任公职,后来响应时代号召,作为一名干部下乡回到村里,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的党支部书记。
爷爷的房间里总弥漫着旧书和墨水的味道,墙上挂着字画。他说话不急不缓,条理清晰,总能将大事小情分析得透彻明白。他是我最早的"政治家"和"哲学家"启蒙导师。从他那里,我懵懂地理解了什么是"责任"、"格局"与"为民服务"。
另一脉来自我的外公。外公是镇兽医站的站长,是另一种意义上的"权威"。他穿着白大褂,背着药箱,方圆几十里的牲畜的健康都系于他一身。他总是风尘仆仆,随叫随到。在外公身上,我学到的是"技艺"与"仁心"。
这一文一武,一内一外,两种不同的家风,像两条丰沛的河流,交汇在我童年的生命里,悄然塑造着我最初的价值观。
第三节 长孙的桂冠与期许
作为家族的长孙,又是外公家最大的孙辈,我自出生便承载了双份的、沉甸甸的宠爱与关注。这份独特的身份,是我童年甜蜜的负担。
在爷爷家,我是他可以带在身边,听他讲道理、练书法的小"传承人";在外公家,我是可以跟他出诊,看他施展技艺的小"学徒"。家里的好东西总是我先得,犯了错也总能得到最多份的原谅。
但这份偏爱并非毫无重量,它背后是无声的期许。大人们时常会看着我说:"你是大哥,要给弟弟妹妹们做个榜样。""咱们家以后就看你的了。"
这些话语,像一颗颗种子,早早地播撒在我的心田。它让我很小就产生了一种模糊的"使命感"和"角色感"。
第四节 爱的经纬:慈爱与劳作的编织
如果说爷爷和外公为我构建了精神的骨架,那么奶奶、外婆和母亲则用最绵密的爱,为我填充了血肉与温度。我的童年,是在她们共同织就的、柔软而坚韧的襁褓中度过的。
我是被奶奶"娇生惯养"出来的孩子。这话毫不为过。直至上幼儿园,每每她背我到校门口,我总要搂紧她的脖子,在她脸颊上响亮地亲上一口,才肯心满意足地滑下她的背,蹦跳着走进校园。奶奶是一位再传统不过的农村妇女,她不识大字,却识得人间最大的道理——与人为善。
这份慈爱,在田野劳作的背景下,显得愈发深沉。
每年盛夏,花椒便像红宝石般缀满枝头,空气里都弥漫着麻酥酥的辛香。这既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一场全家总动员的艰苦战役。天蒙蒙亮,我们便全副武装地钻进花椒地。
母亲是这场战役里当之无愧的"元帅"。她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摘花椒快手,双手并用,手指翻飞,一颗颗花椒果精准地落入筐中,又快又干净。那速度里,是全家的生计和希望。
而最让我至今想来仍觉心疼的,是奶奶。她对花椒严重过敏,一天下来,手臂尽是红肿。可她却是最"固执"的一个。为了多摘一些,她中午从不回家吃饭,总是让我们把饭带到地头,匆匆扒拉几口,便又弯下腰去。那红肿的胳膊在墨绿与艳红之间反复穿梭,无声地书写着"奉献"二字。
我们自家的花椒摘完,战役还远未结束。常常是凌晨五点起床,再上山去帮别人家摘,以此赚取我和妹妹的学费。
但现在回想,那些痛苦的劳作,却奇妙地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,成了我童年最珍贵的乐趣。乐趣不在于劳作本身,而在于劳作间隙的"忙里偷闲"。
正是这爱的经纬——奶奶外婆毫无保留的疼爱,与父母在艰辛劳作中表达的淳朴而深沉的责任感——共同编织了我童年的底色。它告诉我:生活是艰辛的,但爱可以为其赋予意义;劳作是疲惫的,但家人在一起的相互支撑,却能生出最踏实、最温暖的乐趣。
这份混合着泥土、花椒麻香与汗水的童年,让我早早地懂得了感恩与珍惜。它是我理解"天命"的基石——那天命,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召唤,它首先扎根于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,扎根于这具体而微、饱含汗与爱的家。(作者:王钧)